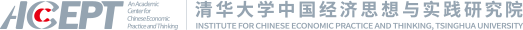蔡昉:在全球化中怎么看政府和市场关系
我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在全球化中我们怎么看政府和市场关系。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全球化的最大的获益者之一。但是这里面政府起了什么作用,或者市场又起了什么作用呢?我想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谈一谈全球化里面的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1990年前后是国际贸易格局的分化点假设从90年代开始,是和之前不一样的全球化。一般认为全球化是货物、资本、思想的全球范围流动,因此通常把资本的流动和全球贸易作为最重要的指标。而说到全球贸易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回归李嘉图”,通过不同的优势交换生产要素,通过产品的流动,各自得到自己的收益。事实上在1990年之前,世界贸易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和前计划经济国家没有参加或很少参加世界贸易,而是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自己跟自己交换,因此形成了产业内的贸易。很显然这个全球化是不能让全球发展中国家获益的,也不能减少贫困。
但是到了1990年之后,中国开始申请加入WTO,并在十年以后加入了。很多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现在也进入到了全球的分工体系中,因此真正有了一个“回归李嘉图”的交换比较优势。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用自己便宜的劳动力,凝结在产品里面去交换发达国家便宜的资本凝结的货物,因此大家都获利。我们以高收入国家为例,其出口和进口的对象在90年之后都逐渐转向了发展中国家,这样真正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交换不同的生产要素,同时也回归到了“李嘉图”原来的增长理论。
以1990年为界,在90年之后才真正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低收入国家发展更快的趋势,因为他们从全球化中真正获益了。这样以世界平均人均GDP水平为标准,可以看到高收入国家相对收入在90年之后是趋于下降的,中等偏上国家的相对收入是提高的,还有中等偏下国家的相对收入增长就更快,同时,最近这些年低收入的国家也保持在他们的相对收入上略有提升,这是一种趋同现象。
过去在理论上一直认为的趋同现象,在1990年之后才有所体现,而且还不能证明真正有很显著的趋同。但从趋势上看,趋同的含义是资本回报是递减的,越是穷的国家,起点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如果能够得到资本的投入,随后的增长速度应该更快一些。1960年到1990年期间,总的趋势线是向上的,也就是说起点收入水平越高,可能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更快一些,至少没有趋同现象发生。1990年到今天,趋同才真正显示出了趋势现象,起点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在随后的增长速度就更快一些,这个趋同就可以导致世界的多极化,世界相对差距的缩小,这是90年这一轮的全球化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如果要再补充一点证据,可以看一看全球贫困的减少,从1981年到2015年,全球的贫困在90年代以来才真正大幅度的减少。主要的贡献是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对全球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贡献了76%,撇开中国,全球的贫困人口也有所减少,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说明了“回归李嘉图”的国际贸易,使得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的国家。
全球化的收益分享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全球化不只是低收入国家获益了。回归李嘉图的贸易,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变得相对更充分地利用,因此出去交换得到了全球化的红利;发达国家有自己的更丰富的资本,它的资本也得到了更高的收益,资本变得更加稀缺了,因此得到了更高的收益。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就直接得到了这个利益,因为经济增长和全球化通过市场立刻就得到了分享。但是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最典型的情况就是资本得到了更多的收益,但是不能自动被所有的劳动者分享,反而出现了中等阶级的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中间技能的产业岗位的消失等趋势。不是因为全球化,也不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竞争,而是因为美国的自动化,与此同时,美国没有好的再分配的社会政策。同样的发达国家,瑞典和美国的收入差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富有的20%人群,在美国掌握财富的84%,瑞典只是30%,可见再分配是有意义的。
在中国,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分享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4年之前,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在这期间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什么增长,但是他们仍然从劳动力市场扩大就业中获益,因为外出规模在大幅度的扩大,只要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挣到的工资就比原来的收入高很多,因此拿转移出来的人数总量乘上平均工资水平,那么他们获得的总收益仍然是巨大的。2004年之后,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工资也就迅速的上涨,尽管这个时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相对慢了,但是他们通过工资的上涨获得了收益。过去发达国家需要更多地靠再分配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本身扩大就业和提高劳动参与率,来提高经济增长的分享。从2010年之后,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人口红利消失了,这意味着资本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要短缺,人力资本改善速度要减慢,资源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也要下降,因此潜在增长率就要下降。下降的同时,如果要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就必须靠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而那种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农产业的急风暴雨式的速度也就不太可能了。因此中国更多地需要充分的竞争,所谓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在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当中,也更加需要社会政策,提高劳动资本,保护弱势群体,包括人们转型和转岗。
政府和市场到底谁优谁劣,或者如何结合,不是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随着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
最后一句话,我写了一个标题叫做一个灵魂两个面孔,经济学除了不能导致自然而然的收入分配改善之外,还有并不能自然而然导致技术无限的渗透,渗透到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