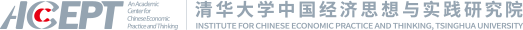刘元春:中国现代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的
我想谈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研究什么?特别是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状况,政府与市场研究的重点应该聚焦在什么地方?因为这里面我们所关注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的大国崛起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事实案例,也引起了中国经济学派的崛起。从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到去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学界都在呼吁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成功,中国会在赶超中间进行崛起?这个问题在我们学术界不是一个新问题。
早到历史学派,然后到结构主义,再到制度经济学,以及再到这几年,新政治经济学已经把这个主题凸显出来了。那么在这个凸显的过程中间,我们始终营造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在传统所设定的这样一些理论范式和关注的焦点可能与中国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为什么呢,体现在什么地方?这可能就是要关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简单的从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落后的国家向现代化进展的进程,也不是简单的从封闭向开放的进程,也不是遵循过去我们先发国家早期工业化的一种模式。
因此当用增长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现在这个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新的成果,来解释中国现象的时候,都觉得有很多的不足。那么这个不足所体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标准经济学里面所设定的最理想的资源配置的范式,与我国资源配置的范式不太一致。而这个不一致,与传统的常识还相违背,这个违背就是我国是在一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上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一种增长。那么很多人会认为这种增长模式可能是一种集权性政治+包容性增长经济制度的结合,但是这种说法很难解释中国所实现的一些新的蓝图,也很难解释中国这种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广度。在上世纪30年代所争论的社会主义市场之间的兼容问题,曾经一度在理论上得出来的是完全否定的答案。但是在这40年里,我们看到它已经给出理论上的一个否定答案,这是我们要思索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市场的产生过程,与其他国家的市场完全不一样,我们并不是遵循简单的市场失灵,引发政府干预,这样的一种市场与政府的二分化。过去政府是市场之母,我们恰恰是在政府这样一种主导下面,不断地创立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地通过开放和改革来形成相对竞争的市场主体、市场制度和市场体系。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并行和替代,不是像西方国家先是有市场,然后是主权国家,先是有第三阶层与民主王权和教权之间的三角斗争,而是在这种政府主导下逐步建立的。这样一种主从关系模式,和简单的发展经济学,和传统的历史学派,和现在的新政治经济学所预设的这种历史过程,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政府在不断创造市场的过程中,如何从培育之手、抚养之手,向服务之手进行转变,而不至于转变为觉醒之手、掠夺之手、管制之手和控制之手。这里面的转型,很多新政治学家做了很多的研究,很多人提出了东亚模式,这是威权体系在高增长之后,特别是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后向包容性政治制度的转型。当下我们的政府在民主集权的过程中,非常强调人民导向性,非常强调要对利益集团的利益打击,因此我国这种政治体系以及制度安排在对可持续增长的关注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不是对现有理论的一种简单依循,这是我们可能要关注的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四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目前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这种战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所设定的目标更为广阔,更为持续。首先就是我们要实施无战争的这种大国崛起,因此我们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我们所提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实行民粹的这种共同富裕,我们期望的是超越目前很多国家所出现的民粹主义,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大创新,要破解李约瑟之谜。我们还要实行无危机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来跨越明斯基的这种时刻。我国目前的政策指向和制度体系的设计,是直接针对着我们在主流经济学里面所提出的很多难以逾越的一些困难和障碍的。因此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模式是不是在这40年里面,已经展现出它完全的本来面目,还是说中国模式只是上半程刚刚开始?而这马上又会引起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果当一种模式,一种实践,还没有完全呈现它的面目,而我们又要急于去进行完全的理论总结和理论诠释,理论能够成功吗?也就是说大象只露出一个头,非要把它的屁股描绘出来,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对于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我们在典型事实、局部规律以及未来前瞻性问题导向的这种研究,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们马上就要上升到主义,上升到范式,上升到体系,过度的理论化,范式化、主义化,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这种实践导向和经验导向的创新。我给我们的同行要泼一个冷水,我们也许不要太着急,我们应当关注过去40年的典型事实,关注过去40年里面与传统理论范式不一致的这种典型事实,然后总结出一些新的规律,而不一定要开宗立派。更重要的是我们依然要问题导向、前瞻性地思考中国所面临的下一步的战略和政策举措,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定位。
我老思考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在新一轮这种技术创新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定位,这个定位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新技术导致了规模递增、边际成本为零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已经使传统的公共品概念大幅度地进行放大。第二,在这种全球竞争条件下,以往以民主国家为界限的这种竞争理论,一下子发生了变化,国内市场结构和国际市场结构的这种对比,使我们对市场结构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三,在目前这种大变局的世界格局下面,世界市场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完美的政府体系,也就是说世界治理的缺失导致民主国家的国家定位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话,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市场结构,政府的能力,政府的掌控模式就会发生一系列变革性的创新。
我想结合中国当下的一些政策选择和政策构建,我们理论工作者是大有可为的,在这里面提供新思维、新战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要做的不仅仅是要总结40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所提供的这种精彩的案例,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中国这样的一头大象它的全身和可能的全身,未来可能显现的这种雄伟的轮廓,再进一步的把握一些前瞻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会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