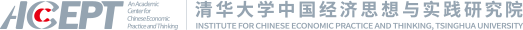房宁: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政府与市场关系
十分荣幸应邀参加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很高兴与各位分享我在调查研究中对当代中国政府、中国制度与市场经济关系观察获得的体验与认识。
中国是在四十多前开始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由弱到强,这其间也伴随着政府与市场、政府机构和官员与企业和企业家关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与西方工业化国家有相同相通之处,但也有所不同。相同之处在于,放开、放松监管,给予社会以自由,从而调动了民间的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而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可以说,中国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建构的产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尤其如此。
中国浙江中部的小城义乌,可以说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一个缩影。1984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义乌,那时义乌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一个山间小城。但就在那时,义乌正在酝酿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大发展。1982年义乌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即著名的“四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给予农民自主生产经营的自由与权利。此后10多年,义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一跃成为闻名世界的小商品生产和交易的中心。曾有两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感叹自然禀赋原本不好的浙江,这个沿海小省的神奇发展。他们说:浙江的崛起简直就是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当然,我们知道,无中生有有其有,莫名其妙有其妙。那就是,政府放松监管,给社会以自由。在中国,放松监管、扩大自由、保障人民权利政策所产生的神奇效果被称为:制度红利。而这个过程是具有普世性的。在亚洲,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是非常相似的,义乌的“四允许”与日本明治时代的“五条誓文”的政策实质是一致的。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西方相比又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政府和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建构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及其无数的官员建立、扶助和培育的结果。和各位分享一个我调研中采访到的真实故事。1984年的时候,浙江玉环县的一位乡长听到中国西南的贵州有个商机。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乡里的一位个体户老板,建议他去试一试,但老板有些为难。这位乡长居然陪着这个小老板一起去了贵州。他们先乘长途汽车颠簸一天赶到省会杭州。但到了杭州没有买到火车票,他俩买站台票上车,在火车上站了30多个小时一直站到了贵州。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政府与企业关系呀!我在多年调研中发现,在中国几乎每一位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的背后都有政府官员,是各级政府和官员们一路扶助,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
概括起来说,中国政府、中国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建构和支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政策调整,筹集初始资本。几十年前,中国是个穷国,老百姓更穷,搞工业化的初始资本从何而来?改革开放之初,通过实行对外开放,从外部获取了一些资金。这方面最开始的举措是1979年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1990年代后通过土地开发获取资金。这种政策措施这是以上海浦东开发为代表的。
第二,建设基础设施。由政府出面建设集中的工业加工区、经济开发区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推动措施。建设工业区、开发区是世界工业化的普遍经验,但也许可以说,近几十年来中国做的最好。从“三通一平”到“七通一平”等等,帮助中国的工业实现了集约化、高效率的发展。当然还有其他的,诸如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方面,中国各级政府被称为“有为政府”。
第三,制订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中国的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很有特色的,这其中也包含了产业政策,通过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后发优势”进行引导和支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能够扬长避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聪明的发展”。
第四,建立健全法制,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为市场经济发育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做了许多,为市场经济发展助力多多。这当中特别值得的提到是,中国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其结果是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亿万受过初等教育的心灵手巧的劳动力。我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带的调研中,对此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于中国政府及制度的建构、支持和扶助,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市场经济实现了一种“战略性发展”,即经过策划和规划的集约和高效的发展。
经过40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系,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现在至少在“瑷珲—腾冲线”以东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的中国了。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政府以及制度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政府机构、政府官员与企业、企业家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新的建构。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的关系,自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了不同以往的重要变化。特别是占中国经济大部江山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制度、政策和政府的约束、管制和限制。应该说近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一个监管回归期。我想,这是当今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另一面,它反映出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企业总是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而政府则肯定要对企业和市场进行监管。这是一对永远存在的矛盾。
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与政府、与制度、与监管体系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过去相互支持、互动到现在的“社会适应性反应”,即规避甚至反制政府的监管。应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重构。
以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关系来说,如果说过去“每一位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背后都有政府官员”,那么今天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许多政府官员背后有民营企业家”。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我认为:现在政府机构特别是基层政府以及官员,与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的关系有这样三个重要内容:
第一,招商引资。现在地方政府非常需要民营企业到当地投资置业,以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指标、GDP增长,仍然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和官员晋升考评中占有重要权重。
第二,资助政府日常运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国地方尤其是市县一级政府的财政长期处于紧运行状态。现在许多基层政府维持城市正常运行的资金不足,有些情况下需要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支持。另外,地方政府的一些重点工程,离开民营企业家的支持和帮助往往就会举步维艰。
第三,官员个人的需要。总体看,中国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的收入和待遇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发生各种寻租行为。腐败,在中国仍然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社会还没有度过工业化阶段腐败的高发期。由于过去的历史,由于在改革开放中政企形成的亲密关系,理清官商关系,建立清廉干净的官商关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腐败是当前中国政府及制度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一个负面因素。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与市场、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建构、促进与互动是早期关系的主旋律,而近期这种关系中的矛盾摩擦与对立因素在不断上升。中国政府、制度与市场经济、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关系的新变化,显示出当前和未来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新因素、新变数。这些新因素、新变数是学术界未来需要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新课题。